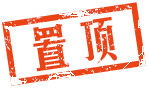|
|
注册成为会员,查看更多专业帖文,更多精华帖文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附件、图片,没有账号?请先注册为会员
×
陪伴你
大四的上学期,正是毕业,找工作,考研紧张的时候。我因肺炎住进了学校校医院。
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里,摆了八张病床。白天有四个人,两位老太太,一个因胰腺炎疼得直叫唤,另一个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老年痴呆症,一个小时内问了我至少五次名字。
我对面床上是一个瘦瘦的中年妇女,令人不敢看她。
她半躺着,全身都在颤抖。手,脚,身体,头,鼻子,嘴唇,甚至耳朵都在动。
晚上只有我和她在。我不停地咳嗽,她也总在呻吟。
我的心情,唉!我希望自己没有任何心情。
第二天早上,我不愿意起来。同学们每天来看我,可是实验课安排得很满,只有晚上下课了他们才会来。所以听到房间门被打开,我没有睁开眼睛。
“你这是搞么事?还不起来?!”一个粗粗的男声炸起来,吓得我一下睁开眼睛,拉紧被子。
是一个中年男子,怀里抱着一个布包,正在掀开那个中年女人的被子,在我看来,很粗鲁地抓着她的胳膊,拽她起来。 “起来嗄!”男人命令道,地道的武汉腔,“过早嘹!几多懒!等下子还要走动走动锻炼下的,还不快起来!”
被掀了被子的女人不停发抖的身体和脸上颤颤的扭曲着的五官,看起来很狰狞,也很痛苦,嘎嘎地叫着,听不明白。
我刷地站起来,“你什么人?你怎么这样对她?”
我冲过去,把被子夺过来给她盖上。一边咳,一边说:“她病成这样,你没看见?”
男人定定地看着我,女人也盯着我,她不能定定的,她一直不由自主地动。
我突然有点后怕。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。
“个姑娘伢,”半晌,那个男人才放下布包,憨憨地笑了,声音也降低一个八度,“我是她丈夫啊。我给她送过早的来了。”
女人又嘎嘎地叫了几声。沙哑难听。
我声音也低了八度,脸发热,“那你也不要这么使劲拽她。她不舒服呢。”
我回到自己床上坐下来。回头看到那位丈夫已经把妻子扶起来,背后垫上叠起来的被子。
我其实一点都不想看到女人的脸,太可怕了。
“你过早没有?我带得多,姑娘伢,早饭不吃对胃不好。”男人把布包里的一个铝饭盒拿出来递给我,半盒子豆皮。
我说,不用了,我不想吃。谢谢你。刚才不好意思。
男人吃着一碗豆皮,瞪着我:“你还小,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。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。生病了就要好好休息,能吃就要吃,吃好了才能把病养好。”
女人在他身边正在用一把超大的勺子喝粥,一多半都被她抖得洒出来,半天送不到嘴里。我看到她面前铺着一块花花的塑料布,身上穿着围兜。
我欲言又止。
男人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:“哎呀!你看看,慢点嗄,都浪费嘹!”
我长吐一口气。
男人回头看着我又说:“你抱怨我不给她喂是吧?”我不说话。
他说:“可是她自己不练习,就恢复得很慢呢!”
他把一双一次性筷子使劲地塞到我手里,说:“吃吧!我这个饭盒从来只装东西的,没有直接拿来吃过东西。”
我一愣。赶紧吃起来。
就这样和他们认识了。
男人对女人说话总是大声大气,动作粗鲁。女人说话不清楚,发出的声音就像鸭子,嘎嘎嘎。尤其笑起来,如果抖着的眉眼弯弯也是笑的话,声音特别难听。
女人的病很奇怪,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和治疗,就是挂水。一天天在恢复,抖动慢慢地减缓。一周后她就可以吃固体的东西,洒在地上的也少了,偶尔还会舍弃勺子用筷子。
每天男人来送三顿饭,吃完了饭就拖着她起床,用脚轻轻踹她小腿,让她在病房的门和窗之间走几个来回。开始她都站不稳,后来可以自己歪歪扭扭地走,也不用扶着病床的栏杆。女人练习走的时候,她丈夫就坐在她病床上,和我闲聊,时不时大叫一声,让妻子走慢点或者走快点,或者够了够了,或者再走一米。
有天晚上同学们来看我,我出去和他们聊到很晚才回去。女人跌跌撞撞地扑到我身边,抓起我的手,放到她床头柜上的一个碗上。
是一碗冰糖梨。
女人在我身边一边嘎嘎嘎地叫着,一边及其奇怪地晃着脖子。
她想要吃吗?
她突然拿起一根筷子,戳到碗里,折腾了几次,什么也没有戳中,就举着筷子晃到我鼻子跟前。
我扎起一块梨,送到她嘴边。她嗷嗷嗷嘎嘎嘎地叫着,胳膊一伸,把梨拍到我胸前衣服上了。
我很莫名其妙地看着她。她看起来急得不行。我于是问,“你想喝汁?”
嘎嘎嘎
“想吃梨?”
嘎嘎嘎
“太甜了要加水?”
嘎嘎嘎
………….
我颓然。看着她不知道怎么办好。
她突然按了铃,护士来了。她就那样扑到护士身上,努力朝外面走。
等了很久,我都快睡着了。突然感觉床前有人拉我的被子。我坐起来,看到颤抖的女人伸到我鼻子前的手上有一张处方纸,上面写着三个支离破碎的字:你吃梨。
第二天早上,男人来送早餐,“要是我在就好了,”男人一边呼噜呼噜吃着热干面,“她什么意思我都懂。你不明白她的意思。”
女人把粘着黑芝麻酱的筷子向男人头上砸去,眼睛眯起来,嘎嘎嘎地……….笑着。
两周之后,女人已经可以自己独立地上厕所,用筷子吃饭也不用围兜。尽管看起来还是不正常,但是她说的词我都可以懂一些,她的笑容已经很象真的笑容了。男人有天非常开心地说,医生说他们可以出院回家了。
女人很兴奋地扒拉着自己的衣服用具,男人一件件整理好。
我觉得,她还没有恢复正常。但我由衷地祝愿他们。我说,希望她在过两三周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
男人收拾东西的手停下来,看了看我。说:“这就是好了。”他几不可闻地叹口气,“完全恢复估计不可能了。都20年了,不变更坏就好。”
我瞪着他和她。20年?
28岁的妻子突然间得了怪病,不能自理,工作没有了,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照顾。男人四处奔波求医,照料病妻幼子。
20年里,妻子始终没有完全恢复,好的时候也就是自己可以走路吃饭上厕所,坏的时候,就是那个可怕的样子,一次一次发病,脾气越来越坏。
清醒的时候也要求离婚,男人不答应。说,孩子需要亲妈妈。“怎么能离婚?那和捏死她有什么不一样?”
也试过自尽。公婆那里也有过压力,也曾不堪重负。
“我们已经习惯嘹!过一段日子就来医院住住。住个把月就回家。呵呵,”他笑得很诚实很满足,“老婆子现在很能干,还能看外甥。过段时间孙子也出来了,她还要看两个。要么是紧,我马上就退休了,两个老的还搞不好么?那不可能嗄!”
写到这里的时候,我眼里热热的。还记得那时他穿着一件灰绿的夹克,他的妻子穿海蓝的小西装,他捉住她的手,塞到袖子里时,一边说,你还是要多锻炼手脚,不锻炼怎么能好起来?还一边叮嘱我,小姑娘伢,生病了要好好休养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莫怕莫怕,怕么事。 |
|